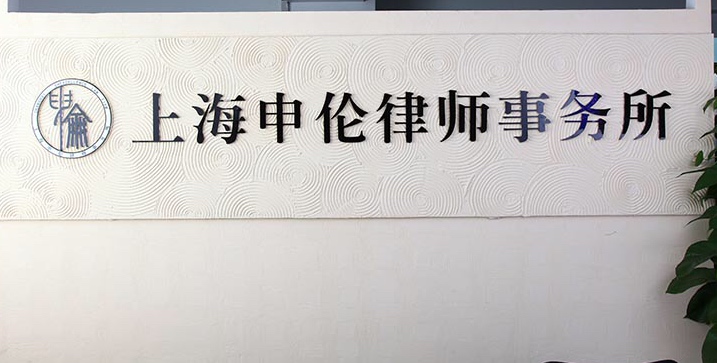 校园虐童事件--法律背后的困境
校园虐童事件--法律背后的困境
笔者:刘晓凤
在这个人与人日益陌生化的社会里,每个公民皆需法律的关爱。2010年温州鹿城幼儿园一老师打孩子致孩子眼睛充血红肿,另一老师用胶带纸封孩子嘴巴;2011年旬阳县幼儿园园长因孩子背不下课文,自己心情不好用火钳烫伤10个孩子;2012年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教师为了好玩揪住孩子双耳离地、因心情不好将孩子扔进垃圾桶;2013年抚顺新华一校,因孩子不小心碰到桌子砸到老师脚遭扇耳光,造成面部外伤左侧枕部皮下血肿,事发之时多名老师在场却无人制止……;虐童事件几乎每年都在上演。客观上讲,在刑法罪名当中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虐待罪和寻衅滋事罪这些罪名都与虐待儿童有关,当虐童行为符合四个罪的构成要件时便可对虐童行为进行相应的刑事处罚。但是为了保护和重视弱势群体和特殊群,2015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的规定,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是指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对其监护、看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实施虐待,并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行为,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行为的犯罪化,不仅可以有效的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还能防止其在非家庭环境中遭受虐待,受到了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以为虐童事件会得到有效遏制,但是2017年11月8日一则消息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可怜天下父母心”,看到自己平时“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孩子在最神圣、最纯洁的校园里遭受的待遇,父母只能运用法律手段对行为人追责,对于孩子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和心理阴影将如何得到化解,这是虐童事件的后遗症。
宝宝权益何处安放?
虽然刑法顺应社会呼吁,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定来遏制虐童事件,但是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根治。运用相关罪名对虐童行为进行定性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运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解决虐童案件的困境;
(一) 公众缺乏相关法律知识
近几年, 尽管媒体总是对虐童案件进行重点报导并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 但是公众对于虐待儿童的相关罪名及相关法律知识的过度缺乏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虐童案件的重视程度并不是特别高, 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运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解决虐待儿童案件的绊脚石。
(二) 部分罪行难以被发现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行为对象都为弱势群体。其中甚至有部分行为对象即使遭受虐待, 也难以被相关部门发现, 故即使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属公诉案件, 依然会有一大部分受虐待的儿童无法得到救济。《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了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 经过五年不再追诉。这也就意味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犯罪行为经过五年后就不能再追诉了。这实质上十分不利于对于儿童的保护。
综合所述, 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第一, 应当加大对虐待儿童相关法律知识的普法力度, 展开具有针对性、多样化的宣传活动, 以期达到重视儿童权益保护的效果。第二, 遭监护、看护人虐待的儿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理论分析并结合相关现实状况, 可以得知该罪名的设立使得大量地虐待儿童的案件可以得到更加妥当的处理, 并且反映出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但是, 适用该罪名来还是会遇到重重阻力, 法律对于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和效果在这些困境面前大打折扣, 这就使得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传统文化有“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的观点,对孩子进行教育惩罚是私人事情,法律无权干涉,说明潜意识里相当认可。媒体甚至一度报道“狼爸”、“虎妈”式的教育培养出名校学子。就算身边真的发生严重虐儿事件,很多人还会以一种“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尊重”别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同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使老师教育引导学生等同于父母教育孩子,父母可以教育孩子为由打骂,则老师也可以,甚至会被冠以“严师出高徒”的美名。在一系列虐童事件中,父母起初发现孩子有打骂的迹象,也都以为是正常教育行为——因为孩子不听话,直至严重伤害出现才引起重视。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正常教育孩子与虐待儿童之间只有一线之差,加剧了其隐蔽性。防控虐童首先需要整个社会观念扭转,需要厘清正常教育与虐童之间的界限,在教育观念上革除落后的管教意识与方式。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人父母,实施虐待行为的“教育者”们,换位思考,假如有一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遭受这样的待遇,你们作何感想?与人为善,那么世人一定会善待你们。